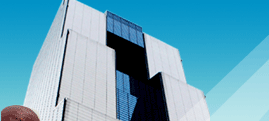春华秋实,大概又到了每年报考研究生的时节了。近些时候,常常在办公室接到各地学生的电话,咨询本所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招生事宜。其实这些电话是打给本所研究生秘书的,但秘书大人不在的时候,常由我代劳了。接到这些考研学生一个个迫切的电话,常常会勾起我对本人当年不远千里、远赴厦门大学考研往事的回忆,那可是一段很有趣、很难忘的经历呀!
我1990年7月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,分配到湖北郧阳师范专科学校任教。这所师专地处家乡丹江口城区的边缘,离南水北调中线起点——丹江口水库6公里,离道教圣地武当山70公里。学校占地400亩,背靠绵延到汉江之滨的丘陵,地势起伏,绿树成荫,风景优美。师专的工作颇为清闲,既无普通中学的升学压力,也没有本科大学的科研指标。在如此轻松自由、毫无压力的环境下工作,除了体验到相当惬意的生活外,还会不自觉地让自己早早结婚生子。比我早一年分配到师专工作的一对原来华师教育系系友,他们当年工作当年结婚,翌年就生下一个可爱的胖女儿。这样的例子在这所偏僻的学校比比皆是。我们学校很小,教职工不多,大家都是熟人。一般情况是这样的:一个年轻人刚分到学校,热心说媒者便接踵至了;如果一个青年人过了25岁还没有结婚的对象,那便成为全校同情的对象;如果一对小夫妻结婚一年多还没有生儿育女的“动静”,那一定会成为举校议论的重大事件。
在如此好的环境下,我早早结婚生子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很多年后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,师兄吴岩老是批评我“早婚早育”,可我从没后悔过。认识女儿她妈以及后来生下我可爱的女儿,肯定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成果了,而这个成果就完成于郧阳师专。
言归正传,说说考研的事情。说我当时考研究生的动机是为了“学术”,为了“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事业”,那纯属瞎话。说实话,我想考研究生就是觉得生活有点无聊,想换个环境。那时,我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,除了每周上6节教育学课之外,别无他事。业余时间,我除了到图书馆翻翻杂志外,还偶尔给一些健康卫生类小报写一点“孩子常做恶梦怎么办?”“男孩女性化怎么办?”之类的小文章,骗一点稿费而已。女儿她妈比我忙一点,除了给学生教“普通话”(其实就是教拼音aoe)外,还兼任“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干事”的重任,常常被邀请作学生演讲比赛的评委,还负责给所有拿普通话合格证的学生盖章。为此,她颇有些成就感,但我看她的工作毫无技术含量。每天下午不到4点,她就跑到我们住的筒子楼前喊我:“打球去!”于是,我们便去办公楼前的空地打羽毛球。乒乓球也是我们的主要运动,只是我输多胜少。那时的朋友很多,我们常常做一桌菜,请朋友同事到寒舍一聚。有时没事情干,我们就骑个自行车到城区乱窜一气。
说心里话,我有时还会很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逍遥生活。特别是我们学校离父母近,我们每周都回家和父母团聚,父母偶尔也会上来看我们。那真是一段再也无法复制的美好时光!
可是人总是难以满足的,特别是年轻人,总是对未来充满着各种幻想。师专的生活虽然轻松,但当我把教育学重复讲了十几篇以后,便对这份工作感到有些乏味了,用现在的术语叫“职业倦怠”吧?当时,我在小报上的“豆腐块”发了不少,甚至还有读者给我来信,请教我“他的孩子得了儿童多动症怎么办?”可我知道我的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研究,充其量就是“科普”,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后来干脆不写了。于是,在女儿她妈的提醒下,我想到了考研。没想到,我考研的过程一波三折。
1992年本是千载难逢的考研机会,因为我前一个学期都没安排课程,可是我自己自告奋勇响应江总书记的号召,到郧县柳陂镇朋儒店子村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便放弃了这次考研机会。出人意料的是,和我一起在郧县社教住在一个房间的汪际边“社教”、边复习,竟然当年考上了
百度搜索更多内容:考研往事
------本站部分文章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若侵犯了您权利,请联系我们。